我创作的意图无非在于以最大限度的自由,用一种生动、可行的方法,将那些反差最大、矛盾最激烈的因素安排在一起,而不是去创造一个天堂。
——里希特
虽说从1963年开始,格哈特·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作品就多次在德国、巴黎、东京等地与公众见面,纽约人却直到1969年才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9位青年艺术家”群体展上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1973年,他在莱因哈德·昂纳施(Reinhard Onnasch Galerie)画廊举办了第一次纽约个展,直到1978年,他才在斯佩罗尼·韦斯特沃特·菲希尔画廊举办了第一次抽象绘画展。
这次谈话颇为震撼人心,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它使我们认识到里希特早期追随波普艺术和其他美国艺术,最后却明确地将自己定位成一个传统的、甚至保守的画家,并认为自己的画中没有任何玩世不恭、反讽或其他种类的理论包袱,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我们对那些只是零零散散在美国办过些展览的欧洲艺术家太缺乏了解了,这一点应该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得到改善。
这个访谈最初是1986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里希特的画室中进行的。访谈是从一系列(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1987年编的)展览目录《格哈特·里希特》中摘录的片段构成的。
本文为本雅明·布赫洛(Benjamin H.Buchloh)对格哈特·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访谈,摘自《国际当代艺术家访谈录》(翟晶译,常宁生校译),文章配图皆来源于网络。
本雅明·布赫洛(Benjamin H.Buchloh)1941年生于德国。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曾获第52届威尼斯双年展艺术批评金狮奖。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教授。

格哈特·里希特
本雅明·布赫洛:1961年林到西德的时候,对20世纪先锋艺术的历史熟悉吗?你对达达主义、构成主义——尤其是杜桑、毕卡比亚、曼·雷、马列维奇等人了解多少了,是否你一到西德他们就成了你的重大发现?还是你渐渐地、没什么计划地学习和吸收了他们的方法?
格哈特·里希特:更多的是后者——一个无计划的、渐进的学习过程。的确,我当时什么也不懂——不知道毕卡比亚,不知道曼·雷,也不知道杜桑。我只知道像毕加索和雷那托·古图索、迪戈·里维拉这样的艺术家,当然,也知道古典主义和印象主义。在东德,上述画派以后的一切事物都被扣上了“资产阶级颓废派”的帽子。1958年参观卡塞尔文献展时,我就是这么纯朴。在那次展览中,波洛克和丰塔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本雅明·布赫洛:你还记得当时丰塔纳和波洛克的作品中是什么特别吸引你吗?
格哈特·里希特:那种“无愧于心”。我对它很着迷,完全被吸引住了,几乎可以这么说这些画是促使我离开东德的真正原因。当时我发现,在我的思维方式中有什么地方是不对头的。
本雅明·布赫洛:你能解释一下这个“无愧于心”吗?听上去它像是一个道德用语,你一定不会是这个意思?
里希特作品:

∧P11, 2014
Chromographic color print mounted on aluminum
16 3/4 × 22 in
42.5 × 55.9 cm

∧Ifrit (P8), 2014
Diasec mounted chromogenic print on aluminium
13 × 17 3/10 in
33 × 44 cm
格哈特·里希特:我正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时我所在的那个圈子总是宣称有某种“道德考虑”总想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座桥粱、一条中间道路,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其结果就是我们的整个思维方式都是折中主义的,在艺术中也追求折中主义。要用个更合适的词表达“无愧于心”只不过避免了激进主义,但并不真实,它充满了虚伪的顾虑。
本雅明·布赫洛:什么顾虑?
格哈特·里希特:嗯,例如关于传统的艺术价值观。首先我注意到:那些所谓的“废料”和“污点”并不是形式主义者的评论,而是一个充满苦涩的真理。一种解放、一个全然不同的新的艺术要旨在此展现。
本雅明·布赫洛:你说过丰塔纳和波洛克是最先对你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并事实上成为促使你离开东德的原因。那么,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你接下来又受到谁的影响?是罗伯特·劳森伯格和贾斯珀·约翰斯,还是依夫·克莱因和皮埃罗·曼佐尼?
格哈特·里希特:嗯,那当然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一开始,我主要是对过渡性人物,如贾科梅蒂、杜布菲和福特里埃感兴趣。对我而言,他们不那么激进。
本雅明·布赫洛:福特里埃——你还能记得对他的什么最感兴趣吗?
格哈特·里希特:厚涂法,不求工整的绘画性,无定形,以及材料的物质性。
本雅明·布赫洛: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吸引你的是绘画中的反艺术冲动——而这同样也是你喜欢波洛克和丰塔纳的原因吗?
格哈特·里希特:是的,还有那些极力想脱离历史的倾向。
本雅明·布赫洛: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你更愿意吸收美国绘画而不是欧洲绘画,更不用说德国绘画了?
格哈特·里希特:德国没什么。有了那么段历史,我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本雅明·布赫洛:那么纳粹时期以前的历史呢?为什么不谈谈那个?
格哈特·里希特:我对那些不熟悉。
本雅明·布赫洛:你第一次看见波普艺术的印刷品是什么时候?你去阿姆斯特丹看过波普艺术展吗?你在巴黎的伊莲娜索纳本画廊看过波普艺术作品吗?
里希特作品:

∧P7 Flow, 2014
Diasec-mounted giclée print on aluminium numbered
17 7/10 × 17 7/10 in
45 × 45 cm

∧Fence, 2010-2020
Giclée print, numbered
10 3/5 × 14 in
27 × 35.5 cm
格哈特·里希特:首先是康拉德·费希尔给我看过波普艺术的印刷品,有罗伊·利希滕斯坦因画的一只火炉,还有沃霍尔的一些东西,他的作品没有利希滕斯坦因那么“非艺术”至少我那时是这么认为。
本雅明·布赫洛:那是在1963年—1964年?
格哈特·里希特:是1963年或1962年。随后我们就带上我们的作品,作为“德国波普艺术家”去巴黎的伊莲娜·索纳本画廊办展览。我们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利希滕斯坦因的原作。
本雅明·布赫洛:利希滕斯坦因一下子就比劳森伯格更能影响你了?
格哈特·里希特:是啊,直到他后来变得有点空洞矫饰,这种影响才消退了,那时,利希滕斯坦因、安迪·沃霍尔、克莱斯·奥登伯格都很能影响我。
本雅明·布赫洛:你能说得更清楚一点吗?他们怎么会对你这么有影响?是那种和劳森伯格作品中的复杂关联,迥然不同的物象的单一性吗?
格哈特·里希特:劳森伯格太做作,趣味性太强,不具备那种震撼人心的简洁。
本雅明·布赫洛:不同于劳森伯格作品中依然可见的、事实上与拼贴原则密不可分的复杂构图相反,我们在利希滕斯坦因和沃霍尔作品能找到的是清晰的物象,像“现成品”。
格哈特·里希特:是的。
本雅明·布赫洛:那么技术方面呢?利希滕斯坦因的完美主义吸引过你吗?
格哈特·里希特:很吸引我。因为那是反艺术的,正好和“绘画”相反。
关于利希滕斯坦:
点,原点,起点,支点 | 利希滕斯坦
本雅明·布赫洛:对你这句话我还是有点意外是利希滕斯坦因和沃霍尔,而不是约翰斯。你一定是以作画方式来判断他们之间的不同的。对沃霍尔和利希滕斯坦因而言,绘画方法、手法本身是作画的关键对象。约翰斯不讨你喜欢的原因就在于他那复杂的手法和他的艺术性吗?
格哈特·里希特:是的。约翰斯还具有一种与保罗·塞尚相关的绘画文化,而我却抛弃了它。所以我甚至画过照片,那使得我得以脱离绘画——绘画妨碍了一切适合于我们时代的表现。
本雅明·布赫洛:但沃霍尔用丝网印刷制作的那些没有个性的图片就没有让你不安吗?那时对你的生存可是个威胁。因为要是有人突然用行动宣布技术已取代了绘画,就会对所有绘画技巧的存在价值造成威胁,不管这些技巧已被简化到什么地步。
格哈特·里希特:也许我对自己不可能、也没办法做的事总是比较羡慕吧。我对极少主义也是这样,那些人也做了我做不了的事。
本雅明·布赫洛:你试过直接用照片吗?——就是说仅仅通过放大,模糊焦点或别的办法赋予了它绘画的性质。
格哈特·里希特:很少,而且只用那些已经画过的图画照片。
里希特作品:

∧Sekretarin (1964) - Hand Signed , ca. 1979
Offset lithograph postcard. Signed in black marker. Unframed.
4 1/10 × 5 4/5 in
10.4 × 14.7 cm

∧Onkel Rudi (Uncle Rudi), 2000
Cibachrome photograph, mounted to Dibond (as issued)
34 1/4 × 19 3/4 in
87 × 50.2 cm
本雅明·布赫洛:沃霍尔创作的理论意义、他对艺术概念激进的开放性态度、他的反审美立场(自从杜桑以来就没有人有过的)也都体现在激浪派艺术的上下文中。那时候,这些一定也都很吸引你吧?
格哈特·里希特:太吸引我了。我觉得它是存在主义的,尤其是激浪派艺术和沃霍尔,一方面又说:“我不能那么做,我只想、也只会画画。”所以,你是一边将自己的创作与反审美冲动相提并论,一边又坚持做个画家。对我来说,这真是个典型的绝对矛盾,而你的创作却必须从中得到发展。
是啊,这很难理解,但我觉得没什么好矛盾的。我不过是以不同的手法做了同样的事,和他们相比,我的方法不那么惊人,也不那么激进而已。
本雅明·布赫洛::换句话说,由杜桑引入、沃霍尔复兴的那种对艺术生产活动的否定是你从不能接受的?
格哈特·里希特:是的,这仅仅因为艺术生产是无法否定的。只不过不再仅仅是用手制造物品的才能,而是一种观看、并决定将看见什么的能力。至于该怎么把它做出来,和艺术或艺术才能都没什么关系。
本雅明·布赫洛:1966年你开始画抽象的色彩图标时,和当时出现的极少主义有没有什么关联?它也参与了和美国主导地位之间的对峙吗?或者它是建立在这里的杜塞尔多夫画派狭窄的地方性小圈子基础上的个人发展?也许它在不经意间受到了帕莱尔莫的影响?
格哈特·里希特:它当然受到过帕莱尔莫及其趣味的影响,后来又受到极少主义的影响。但1966年我画色彩图标时,受波普艺术的影响更多。那帮人画了些有形状的色卡,这些漂亮的色卡的效果在于它们正与新构成主义,如阿尔珀斯等人的努力相反。
本雅明·布赫洛:那时候你知道巴奈特·纽曼吗?
格哈特·里希特:不,但后来我却喜欢上他了。
关于纽曼:
是谁在害怕红黄蓝 | 纽曼
本雅明·布赫洛:所以你的抽象作品事实上是对欧洲抽象传统的一次冲击。
格哈特·里希特:那是对人们用不诚实的敬畏来赞誉抽象主义的那种虚伪和虔诚的冲击,他们把那些方块块当作教堂艺术的同类物来崇拜。
本雅明·布赫洛:反之,极少主义的抽象却使你很感兴趣?
格哈特·里希特:是啊,极少主义画上两三个灰色的色彩图标。在我的色彩图标,尤其是比较晚些的作品中,可能体现出了观念艺术的理论和教学方面的影响,但事实上,这只是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需要我不知道怎样有意味地组织颜色。我只想画得尽可能地漂亮、清晰。
本雅明·布赫洛:你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翻画的那些照片的确有种反艺术性,它使画家的主体性、创新性、原创性都变得毫无意义。所以说,你是在某种程度上步了杜桑和沃霍尔的后尘,并且你作品的主题选择显示了随机性,所以它使得内容不再重要了。
格哈特·里希特:我选择主题并不是随机的,为了找到合用的照片,我可费了不少事。
本雅明·布赫洛:那么,每次选择都是很复杂的,并且都有明确的动机了?要是这样,我在巴黎编目上发表的评论就很成问题了,我当时说你完全是随意选择照片的。
格哈特·里希特:也许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偶然、随机的还更好些。
本雅明·布赫洛:那些肖像作品是按什么标准选择照片的?
格哈特·里希特:当然是按内容。可能在以前我否认过这一点,我说:我的创作不考虑内容,只是不动感情地画一幅照片,然后把它挂出来而已。
本雅明·布赫洛:现在有些评论家一心想证实你强调了肖像画内容的重要性,乌尔里克·卢克和尤尔根·哈顿提到“死亡系列”飞机象征着死亡,“金字塔”事故也都象征着死亡。而我觉得,要在绘画中构建起持续的死亡主题是件相当牵强的事。
格哈特·里希特:你认为我不过想找点惊人的主题,而我自己却根本无动于衷?
里希特作品:

∧Haggadah, 2014
Diasec-mounted chromogenic print on aluminium
23 3/5 × 23 3/5 in
60 × 60 cm

∧EIS II, Ice 2, 2003
Screenprint, Poster
44 3/4 × 34 1/2 in
113.7 × 87.6 cm
本雅明·布赫洛:在这个意义上我承认一切选择都不会是随意的,一定有某种态度在内,即便是复杂而无意识的态度。但一个人只要见到你在20世纪60年代画的肖像画,我认为他就很难在其中构建起持续的死亡主题,《8个见习护士》那张倒也罢了;《48幅人物肖像画》那张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其中找到了死亡主题简直无聊;“智利风光”和“金字塔”有什么关系?“城市”和“山”又有什么关系?那些图像志的元素的确可以结合起来,但却不是在有所谓“死亡主题”传统图像志意义上的结合。在你的画中构建传统图像志似乎是荒谬的事。
格哈特·里希特:也许谈“死亡主题”是很夸张,但我想总和死亡、痛苦这类事情脱不了干系。
本雅明·布赫洛:但这些都不是影响选择的决定性、动机力量。
格哈特·里希特:那我可不知道。要我重构起当时的动机是很难的,我只知道总有一些原因促使我去选择某一张照片,去表现某一个事件。
本雅明·布赫洛:除了其内容不再和“画像”相关之外?那你又有一个矛盾了比方说,你很清楚死主题不能用单纯的画像来表达,你却试图去这样做,做的同时又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格哈特·里希特:嗯。首先,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一幅死狗的画不过是画了一条死狗,只有当你想表达某种弦外之音,或内容过于复杂,仅用图像无法表达时,才会遇到困难。但即便如此,画像也还是有它的意义。
本雅明·布赫洛:你知道自己的选择标准吗?你怎么选择照片?
格哈特·里希特:我找那些适合我、又有现实意义的照片。我选黑白照片,因为我发现它比彩色照片更有力度、更直接、更少艺术性,所以也更可靠。同样道理,我也更喜欢那些外行拍的生活照、那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和快照。
本雅明·布赫洛:那幅《阿尔卑斯山》和那幅《城市》呢?
格哈特·里希特:那时,我不想再画那些华丽的照片,想画点其他东西也不想明明白白地陈述什么了,我就画了它们。这些死去的城市、这座阿尔卑斯山吸引了我,它们有堆积的碎石、无言的废弃物,它们吸引我去传达某种更为普遍的内容。
本雅明·布赫洛:若是你果真重视这种题材,你又为什么同时进行抽象作品的创作呢?比方说色彩图标,或其他与那些具象性作品并存的抽象作品。这种同时性让你的大多数评论家头疼,他们将你当作一个通晓了一切手腕和技巧、深谙所有图像志惯例,却对之不屑一顾的画家。这也是你的作品现在对一些人特别有吸引力的原因。看上去,你的创作似乎以某种庞大、反讽性的回顾方式展现了整个20世纪的绘画。
格哈特·里希特:这的确是个误会。我没什么手腕、反讽或巧喻,恰恰相反,我几乎像个门外汉一样惊异于自己表现方式的直接,惊异于自己所思所为的易于理解。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你说在具象性和抽象性之间有矛盾。
里希特作品:

∧Cage f.ff.
Edition 2/5, Colour print on aludibond behind plexiglas
35 2/5 × 35 2/5 in
90 × 90 cm

∧P16 Flow, 2016
Diasec-mounted chromogenic print on aluminium composite panel
39 1/2 × 78 3/4 in
100.3 × 200 cm
本雅明·布赫洛:我们以你首批作品中的《桌子》为例吧。《桌子》包含了两个因素一是完全的抽象,暗示性和自我反思一是再现。这的确是20世纪的巨大困惑之一在绘画再现和自我反思间的矛盾或对立,而在你的创作中,这两种立场却被拉到一处。你不是想以这种方式来表明它们二者都是不健全的,都已无处存身了吗?
格哈特·里希特:不会无处存身,但从来都不健全。
本雅明·布赫洛:按什么标准说它们不健全?是表现性吗?
格哈特·里希特:按我们对绘画的要求。
本雅明·布赫洛:能就这种“要求”下个定义吗?
格哈特·里希特:绘画应当更加完整一些。
本雅明·布赫洛:所以,你会反驳人们对于你的指责,说你用一种反讽的态度默认了绘画的无效?
格哈特·里希特:是的。因为我知道绘画并非无效,我只想让它更完整一些。
本雅明·布赫洛:换句话说,再现和自我反思的同时并存不是超然于这二者之上,而是想以不同方法认识绘画的要求?
格哈特·里希特:大概是吧。
本雅明·布赫洛:所以,你认为自己并未将那种历史性的分裂敌对、七零八落的局面继续下去。在那种局面下,一切绘画技巧都不再真正有效。
格哈特·里希特:并且,我还将自己看作一个庞大、宏伟、丰富的绘画,至全部艺术文化的后继者。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文化,而它却始终没离开过我们,在这种情形下,要想不去恢复那种文化,或简单地放弃它、任它堕落都是相当困难的。
本雅明·布赫洛:从创作伊始,你就发觉自己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你是不是认为自己近来的创作会帮你在这个困难中继续发展——也就是说,一边表现出如你在照片中所见的大众文化的真实情况,一边却使之与你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在的精英文化和杰出人物的圈子相对立?在这个意义上,你正是用辩证法来创作,并且使自己一直处于这种矛盾中,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仍然是你的处境吗?还是只在20世纪60年代是这样?
格哈特·里希特: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看待这个境况。
本雅明·布赫洛:但你引证塞尚时所说的话却正是这个意思。那时你说:“对我来说,快照都比塞尚的最优秀的作品强。”我觉得这句话显然表达了这种矛盾。
格哈特·里希特:是的。但这并不证明我立即就能用绘画来改变点什么,当然也不意味着我不用绘画就能改变什么。
本雅明·布赫洛:为什么你这么坚持否认你自己作品中的政治性呢?
格哈特·里希特:因为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因为艺术全然是另一码事,因为我只能去画画。要是你愿意,称这个为“保守”就是了。
本雅明·布赫洛:但是,也许限制创作的媒介不仅显示了保守,还包含了一种批评就是对像波依斯这样的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提倡的“即时反应政治”提出质疑。
格哈特·里希特:我当然愿意以我对绘画的限制批评那些让我不愉快的、不只考虑绘画的做法。
本雅明·布赫洛:所以你没有对“艺术应当对政治批评保持清醒的认识”这一要求的有效性完全绝望?
格哈特·里希特:当然。但关键在于我只能从自己的能力、基准和潜力出发。
本雅明·布赫洛:你要申明哪些东西是不可更改的?
格哈特·里希特:大部分都是不可更改的。
本雅明·布赫洛:甚至你的抽象绘画作品也有内容吗?
格哈特·里希特:是的。
本雅明·布赫洛:他们不是对内容的否定,也不仅是绘画本身的真实性,更不是对当前表现主义的反讽性阐释?
格哈特·里希特:不是。
本雅明·布赫洛:不是对抽象语言的扭曲?不是反讽?
格哈特·里希特:从来不是!你想问的究竟是什么?要是我的画没有内容,你认为它又是什么?抽象表现主义又在什么地方和我对立?
关于罗斯科:
等待,不要迟疑 | 罗斯科
本雅明·布赫洛:显然他们的作品的主旨是不同的。比方说马克·罗斯科,他用稀薄的渐变色来表现空间感,而你却很快抛弃了空间感。深度、影像模糊、光泽感、超然性——这一切都被真实再现出来。而且,在罗斯科的创作中,色彩关联是相当受重视的他以一种清晰的计算、仔细的区分使两个,至多三个色度或色调关系形成呼应,结果产生了一种明确的色彩和谐,这种和谐又进而制造出心理的、情绪的效应。
格哈特·里希特:这在原则上和我没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手法造成了不同的效果。
本雅明·布赫洛:不是这样。要是色彩的这种制造情感和精神性品质的能力一边到处显现,一边又到处受排斥,它就会一再自我取消。如果它造成了这么多组合,这么多、这么善变的关联的话,人们就没办法再谈论色彩序列的和谐了。而在你的作品中,人们也没办法再谈构图,因为不论就色彩还是构图而言,它们都不具备什么有序的关联。
里希特作品:

∧Ohne Titel (9.3.97), 1997
Watercolour on paper
4 9/10 × 6 7/10 in
12.5 × 17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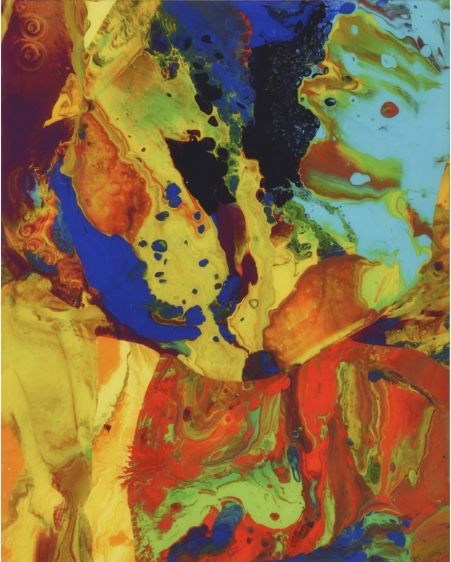
∧Bagdad I (P9), 2015
C-print
19 7/10 × 15 7/10 in
50 × 40 cm
格哈特·里希特:我可不会这么看问题。我不认为我的作品中已没有构图或色彩关联了,只要我将两个色彩样式放到一起,它们之间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关联。
本雅明·布赫洛:是的。但这些是以不同方法、不同关联原则构成的不同样式。要是人们有意认可,那么至绝对的否定也是一种构图。但你抽象作品中的一切却都在致力于对传统的、关联性秩序的超越,因为作为一种可能性,结构不同的各元素的无穷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
格哈特·里希特:是的。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仍然不得不使一切都有正确的关联。画得越深人,关联就越困难。开头的时候,一切都还简单明了,但渐渐地,关联会使那种套路,也就是那种不同于随机性的东西显得很合时宜。
本雅明·布赫洛:这是当然。但这也是一种不同的感觉,从而也是不同的样式,也许显然与传统的构图和色彩关联截然相反。
格哈特·里希特:也许吧。不管怎么说,我的方法或我所期盼的东西,也就是促使我去画画的动机,是反叛。
本雅明·布赫洛:你期盼的是什么呢?
格哈特·里希特:一些自然浮现的东西。这些我从不认识、也无法计划的东西比我更优秀、更聪明、更具有普遍性。其实在那张《1000或4000种颜色》中,我早已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进行了尝试。我期盼着一张画会自然地浮现出来。
本雅明·布赫洛:哪种画?
格哈特·里希特:某种更精确、更真实的表现了我们状况的画。其中应该有某些预见性的东西,有可以作为建议来理解的东西,但又不仅仅止于此。不说教,也不是逻辑,而是十分自在、毫不费劲地浮现出来,把所有的复杂性都抛开。
本雅明·布赫洛:你最优秀的作品无疑具有这些品质。它们显得毫不费力,又显出作画过程的充满激情,并且体现出客观性与精湛的技巧。但我们还是回到“内容”的问题上来吧。如果一幅画强调的显然是方法,你又怎么能说涂抹模糊的画面、处理颜色的技巧并不显现单纯的创作过程或单纯的物质性?要是你并不重视这些,你就不会以那种方式用色了。那就意味着要把不考虑颜色、不考虑构图或结构、超越单纯的物性之上的那种创造超然意义的可能性当作绘画了。我认为你的画已经将过程因素当成一种创作可能性考虑进去了,但又和曼·雷不同,你并不将这种过程因素当作绘画的惟一方面,而是当作绘画众多特性中之一种。
格哈特·里希特:我为什么要自找麻烦,把创作弄得如此之复杂呢?
本雅明·布赫洛:也许因为对你来说,像一张目录那样列举绘画的方方面面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你真正感兴趣的是绘画的“修辞手法”及其分析。
格哈特·里希特:如果我不过想展示一下物质材料,那么粗糙不平的黄色画面如何与蓝绿色背景形成对比?又怎么形成或引发感情呢?
本雅明·布赫洛:感情?你真以为你的画能引发感情?
格哈特·里希特:当然,还有审美愉悦。
本雅明·布赫洛: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也从中得到了审美愉悦,但感情却一点也没有。
格哈特·里希特:那什么才是感情?
本雅明·布赫洛:必须有明确的情感、精神、心理特征。
格哈特·里希特:我的画就有这些。
本雅明·布赫洛:还好,只在那些最薄弱的部分。
格哈特·里希特:其实,你并不相信沉默的笔触、绘画及绘画元素的语言真能实现点什么、说点什么、表达什么渴望。
本雅明·布赫洛:渴望什么?
格哈特·里希特:人们失落的品质、一个更好的世界、远离苦难与无望。
本雅明·布赫洛:渴望能一边坚持文化观念沉思的特点,一边又保持可信度吗?
格哈特·里希特:还可以称之为拯救,或者说希望。希望我能用绘画做点什么。
本雅明·布赫洛:但这也是个普遍存在的司题从哪方面人手呢?认知?情感?心理?政治?
格哈特·里希特:也许都有——但我怎么知道呢?
里希特作品:

∧Schwarz, Rot, Gold III, 1999
Synthetic raisin varnish behind glas
15 2/5 × 15 2/5 in
39 × 39 cm

∧Blech (Sheet Metal), 1988
Oil on canvas
7 9/10 × 10 3/5 in
20 × 27 cm
格哈特·里希特:我不谈什么社会政治关系,原因就在于我只想作画,不生产意识形态。只有画本身才能使一幅画成为好作品,其中的意识形态却不能。
本雅明·布赫洛: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看得出你是将色彩当作一个物质过程来处理的,这样,色彩就成了你运用那些绘画手法要展现、转换的主题,虽然画面构成不一,这一点却是不变,它告诉我们画是怎么画的、用的什么手法。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外在因素能决定色彩的外观或结构,所有的色彩现象都是自足的。这样阐释你的画还会过于狭隘吗?
格哈特·里希特:是的。因为我并不是为了作画而作画,而那些漂亮的技术、手段只有被我拿来表达点什么时才有意义。
本雅明·布赫洛:除了信仰,那些画还传达什么?
格哈特·里希特:一幅画,从而也是一个模式。现在我回想起你对蒙德里安的阐述他的画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的模式,同样,我也可以将自己的抽象作品看成某种比喻、某种可能的社会关系的形象化。以此观之,我创作的意图无非在于以最大限度的自由,用一种生动、可行的方法,将那些反差最大、矛盾最激烈的因素安排在一起,而不是去创造一个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