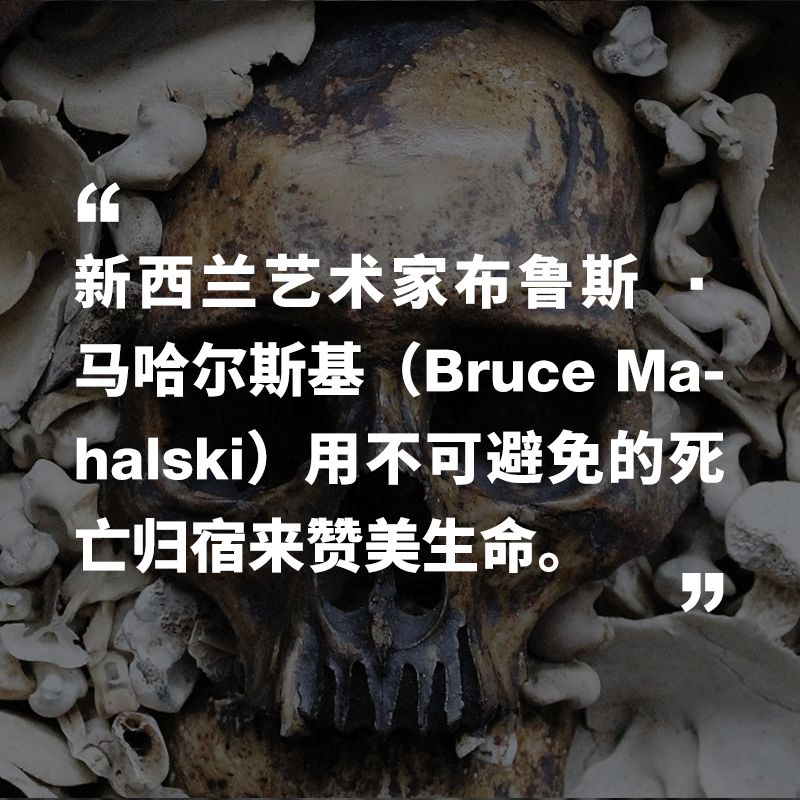
本文原载于 VICE 新西兰
骨头或许会让我们想起死亡,但新西兰丹尼丁市的艺术家布鲁斯·马哈尔斯基(Bruce Mahalski)从中看到的却是生命。十年来,马哈尔斯基不断尝试、实验,他称之为 “纹理骨雕”(textural bone sculpture)。
马哈尔斯基的灵感来自博物馆展览,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展品,他用动物的遗骸来创作出吸睛的作品,材料包括兔子、负鼠和鸡的骨头。不过,真正让马哈尔斯基脱颖而出的,是他还敢用人的骸骨和头骨。

Te Hopu(鲷鱼)
在马哈尔斯基看来,护卫逝者尊严是至关重要的,其基础就是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不同物种。于是他把人骨和动物的骨头并列,从而把人类放回自然界应有的位置。他认为:“我们不是进化的顶峰,只不过是另一种冒充上帝的有害生物。”

鸡和兔
在成为艺术家很久之前,马哈尔斯基是一位收藏家。他从小就会捡来各种贝壳、骨头、昆虫和他最喜欢的蟹壳来装满巧克力的包装盒。对此,他认为都是父母的影响,他父亲是一位医学专家,母亲是心理学老师,两人都分别有一系列珍贵的生物藏品。
成为收藏家兼艺术家的想法让马哈尔斯基非常兴奋。虽然有艺术上的天赋,但他坚称自己真正的热情还是收藏,只是很幸运地找到了一种让收藏和表达变得理所应当的方式。
在 Rim Books 出版的马哈尔斯基的新书《生命的种子》(Seeds of Life)中,他跟作家克雷格·希尔顿(Craig Hilton)讨论了创作的过程和人类脆弱的生命,以下为书籍节选。

克雷格·希尔顿:你为什么要把人骨和动物的骨头混在一起?
布鲁斯·马哈尔斯基:我这么做是想试着把我们放回自然事物的合理秩序中,现在还为时未晚。
我认为,人类正在完全毁灭自然环境的边缘摇摇欲坠,因为我们过于在乎自我,忙着存钱来解决污染和气候变化的迫切问题。有很多的一厢情愿。基督徒和穆斯林受到的教育是,自然由上帝创造,用来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很多人还相信,圣经中的千禧年即将到来,所以就算破坏环境也没关系,因为世界反正也要迎来末日了。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无神论者又把科学视为一种新的宗教,认为新发明能够救人类于水火之中。总有人会发明出生产清洁 “廉价” 能源的方法,我们将能够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一些信教人士认为人类的生命高于其他万物,但我认为这种物种歧视的态度正是当前很多问题的根源。我看不出来人类、老鼠、猪的骨头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我知道,我就是一种动物。问题是怎样成为更好的动物而已。我用我的艺术来试着跟人群对话。我们正奔向灭亡的悬崖。在坠崖之前,我希望我们能够拐弯。

你觉得你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
对于骨头和其他有机物质,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我认为我现在还只是蜻蜓点水。我想做更大的作品,用骨头的纹理覆盖整面墙。围绕着我的收藏和艺术作品,我正准备在丹尼丁创办一个小型私人机构,就叫 “自然奥秘博物馆”(The Museum of Natural Mystery)。

当你在创作中需要做决定时,融合不同物种是不是一种需要,或者说是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完全取决于作品。在一些跟地理位置相关的作品中,所有骨头都来自那个地方,什么物种并不重要。骨头就像是某个地方全体动物生命的 3D 图示。在其他作品中,我可能就关注某一个物种,比如 “脘病毒灾难”(Prion Wreck,2012)是用来纪念一场波及那些鸟类的自然灾害。“兔头架 #1”(Rabbit Skull Rack #1,2014)则更像一份强调这些动物多么常见的声明。但是很多作品里会混合不同动物的骨头(有时候也有人类的),用来更高调地说明我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我们有责任去努力捍卫整个环境,同时去承认、尊重很多人认为丑陋无用的一些动物。

Mere de Rat(鼠妈妈)
你认为最终的作品是一种物种的融合吗,创造一个新物种?
不,绝对不是。更像是特定时间空间中的一张地图。
尤其是中心摆了头骨的那些作品,你是在赋予它们生命吗?让它们再次发声?
我没有在赋予生命,但的确有试着让它们发声。我的使命就是拓宽大部分人的审美范围,让他们更深刻地去欣赏其他生命形式,并且想要去保护。现代对美的概念是由生理和文化决定的。我们喜欢评判其他动物,标准就是它们有多么符合我们作为哺乳动物的固有偏好。举个例子,大部分人认为毛皮比鳞片更美。我们是有偏见的。不能说因为我们认为它们不好看,就随意地抛弃生物群中的一大部分成员(昆虫和鱼都是典例)。

你做这个的动力是什么?
我对社会的那种脱离现实又过于自信的道德责任感吧,以及作为(白种男性)人类的存在主义上的深切内疚感。
你可以在 这里查看布鲁斯的更多作品。

Oves Dei —— 绵羊女神


信天翁


